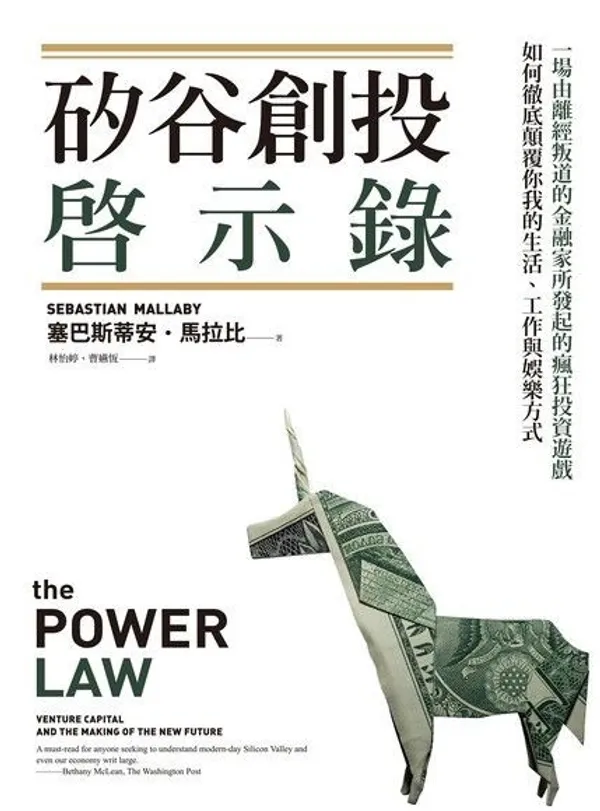創造 IT 產業高達 1/3 市值的明星創投為何殞落?凱鵬華盈衰落給領導者的啟示
整個 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,凱鵬華盈一直是領先群倫的創投公司,據說從網際網路創造出來的市值中,有高達 1/3 來自它的投資組合公司。到了大約 2015 年,經過一連串平庸的投資之後,凱鵬華盈已然從檯面上消失。
由於創投績效的路徑依賴之故,凱鵬華盈的走下坡特別引人注目。創投業者因為支持勝出的新創公司而功成名就,進而有了在下一批潛在贏家中優先挑選的機會。有時候,因為創業家們看重知名投資人的認可,所以可以給後者折扣價。這種自我強化的優勢──聲望帶動績效,而績效又帶動聲望──引發一個微妙的問題。這些佼佼者是真的擅長創業投資,還是只是搭著名聲的順風車?
凱鵬華盈的故事演繹了學術研究已經證實的事情:名聲很重要,可是無法保證成果。每一個繼起的世代都必須重新去贏得自己的勝利。
凱鵬華盈的名聲一落千丈,一般被認為是某個糟糕透頂的投資決定所致。從 2004 年開始,這家公司便在追蹤所謂的潔淨科技(Cleantech)新創公司──押注在對抗氣候變遷的技術上,從太陽能、生物燃料到電動車都涵括在內。
2008 年,凱鵬華盈加倍力道,把一個全新的 10 億元成長基金拿來專做此一領域的投資,這個承諾混合了理想主義與一廂情願。凱鵬華盈的主要合夥人約翰.杜爾毫不掩飾他公開承諾拯救地球的感情,他喜歡引用還是青少年的女兒瑪莉的話:「爸,這是你們這個世代造成的問題,你要解決它。」
同時,杜爾也堅持發展綠色科技有財務面的論據,他提醒大眾,能源是規模達 6 兆元的產業。「還記得網際網路嗎?」他在 2007 年如此反問。「告訴各位,綠色科技──環保綠化──的發展比網際網路更大。」
不管潔淨科技的重要性如何,它對創投業者來說都是一個棘手的領域,而杜爾也不該告訴大家規模龐大的市場就等於有利可圖的市場。做風力發電、生物燃料或太陽能板的新創都是資本密集的公司,使巨額虧損的風險增加;他們的計畫需要數年時間才能成熟,故而壓低少數成功者的年均報酬率。
面對龐大的資本需求與拉長的投資期間,為了有所彌補,理論上,潔淨科技的投資者會以較低的估值進行投資,並且要求取得更多股份。不過,在青年起義所確立的「友善創辦人」風潮下,杜爾不想這麼做。
錯上加錯的是,杜爾初試啼聲的潔淨科技投資,聚焦於缺乏明顯「護城河」保護的生意:製造能源的太陽能和生物燃料項目,都是價格極具周期性的大宗商品。
當油價在 2008 年夏天崩盤時,杜爾的替代能源投資也一敗塗地。在那之後,中國補貼的太陽能板大量湧入市場,加上開採天然氣的「壓裂」(fracking)技術問世,進一步拖垮能源價格。而同時間,在這一連串市場重挫之外,還有一個政治錯誤來攪局。杜爾高估了聯邦政府履行承諾對碳徵稅或進行管制的意願。
對凱鵬的有限合夥人來說,這是個悲慘的結局。第一波綠色投資的表現特別糟糕,2004、2006 和 2008 年所募集的創投基金因此蒙受虧損。某個有限合夥人投資一檔 2006 年的基金十幾年,抱怨說他虧掉將近一半資本。
凱鵬的第 2 波潔淨科技投資始於 2008 年的綠色成長基金,表現得比較好。公司瞄準有護城河護體的業務,繳出幾張亮眼成績單:截至 2021 年,植物肉公司「超越肉類」(Beyond Meat)獲利 107 倍,電池製造商 QuantumScape 獲利 65 倍,而太陽能公司 Enphase 則已獲利 25 倍。這已經足以製造出至少一個排名矽在產業前 1/4 的創投基金。
可是凱鵬的整體績效還是不見起色。回到它的鼎盛時期來看,2001 年,柯斯拉和杜爾分別名列《富比士》最佳創投人榜的榜首及第 3 名。到 2021 年,杜爾掉到 77 名,而且沒有其他凱鵬華盈的人物進入前百大。
當壞消息開始傳出時,大多數凱鵬華盈的有限合夥人仍堅持與公司站在一起,證明路徑依賴的威力強大。一開始,他們寄望古老的魔法能復甦。再怎麼說,杜爾對 Google 及亞馬遜的勝舉,使他成為有史以來最成功的創投家,而且他還是很有個人魅力。
後來,有些有限合夥人基於一個不同的理由繼續投資:他們看重這家公司在矽谷響噹噹的名聲,即便內部人士知道這個所謂的名聲已經蒙塵。
比方說,有一個組合型基金(fund-of-funds)便吐露,它自己的投資者──小型簡單的退休基金──很讚嘆他們的資本是由赫赫有名的凱鵬華盈來管理:若沒有組合型基金作為媒介,這是他們做夢都不可得的那種尊榮管道。
可是到了 2016 年,即便這些追逐名牌的投資人也開始漸漸離去。凱鵬華盈的招牌已經沒有威望可言,而光環褪盡的杜爾也離開了投資合夥人的職位。
用這套潔淨科技的標準說法來解釋凱鵬華盈的困境,只能說部分正確。這家曾經在第一波網際網路浪潮時大賺一筆的公司,鼓吹莫非定律與梅特卡夫定律的威力,卻一頭栽進缺乏這類神奇優勢的產業,令人瞠目結舌。
而這個故事還有另外一面,呈現出關於創投產業的一個微妙真相。許多其他個案研究證實:創投基金打的是團體戰,往往要動用好幾個合夥人才能談定一次成功達陣的交易,而交易完成後,領軍打仗的投資人也並非總是帶領投資組合公司的舵手。創投團隊若要高效作業,合夥企業就必須要有對的文化。而這正是凱鵬華盈處理極為不當的地方。
(本文出自《矽谷創投啟示錄》,商周出版)